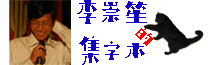我做了一个梦,很荒诞。
我独自驾着一辆马拉的战车,狂驰,来到一片死寂灰暗的荒原。突然,马脱缰了,失控的战车在原地打了一个转,像早有预谋似的,在它静止的一瞬,把那个将命运系在一根轮轴上的傻瓜甩了出去。于是我飞了起来——其实在梦里飞翔是一桩再平常不过的事了,只不过别人飞得自由,我飞得恐惧。

我得以看清大半个荒原。天空铺盖着墨汁一样浓稠的乌云,缓缓地搅动着,粘在天上,恶心得如同老太太牙缝里挤出的黑色奶油,好像马上就要一滴一滴地垂下口水来;在某个方向的天边燃烧着一团奄奄一息的火,隔着乌云泛着污浊暗红的光,好像淹透的咸鸭蛋黄捣碎在臭烂的泥里,晨曦?或是晚霞?谁知道,也许那竟是北方;大风起了,吹碎了我耳际的发梢,根根发丝恐惧的颤抖,但我什么也听不到,我前额的头发刺进眼睛里,我不想闭眼,但我什么也看不到,我的双手在我指尖所能触及的空间里胡乱的拨划,想抓住任何一个牢靠的东西,好挽救我那在风里飘摇的身体和命运,但我什么也触不到……

我的身体猛地震悚,醒了。寒冷沿着躯干流动,仿佛是一条泛着清冷绿光的毒蛇吞食一只兔子,把长着冰冷尖牙的嘴巴撑得夸张的大,慢慢地,一点一点地往胃里咽,从脚到头。“靠车窗坐着真难受!”我这样想着,头偏向车窗外,于是我看到了,看到了另一个披着白色斗篷的,匍匐着的,向后爬动着的,真实的,冬天的“荒原”。我哆嗦了一阵:“好冷!”

中原与荒原仅一字之差,有时我甚至觉得它们之间没什么差别,就如我在返家的长途大巴上看到的那片白色的土地一样,只有那偶尔会从雪层下钻出来,桀骜而孤独的守望在一片绝无生气的雪原上的坟茔,会突然跳到我的面前,像一个辩论家一样板着一副阴森的脸,教训我道:“我是一户中原农民的先人,我在这里守望维系家族命运的田地!”于是我知道,这里就是中原,就是家乡了,这里有扛起中华五千年脊梁的红肿的肩膀,这里有刨碎无数次饥荒的锈烂的锄头,还有被北京的民俗家们视为民族精神的纯粹的传统——落叶归根。在这里的农村如果有人去世,是要葬在自家的田地里的,也许是因为中原的农民活着的时候一辈子都在料理土地,也靠那片黄土养活一辈子,那是全家人的衣食来源,是生命中一切的根,是叶落必归的根,或者也许是因为怕逝去的灵魂找不到自己的家,成为荒野的孤魂,毕竟不论家乡的土地多么贫瘠,总是能让人感到安心。
人不能离家太远,太久,不然就和做噩梦一样,仿佛独自驾着一辆马拉的战车,将命运系在一根轮轴上狂驰,在一片死寂灰暗的荒原玩命似的乱闯,也许瞬间就会被命运抛弃在飘摇的风里。

“老乡……”邻座的一个中年人用右肘顶了顶我的左臂,“现在几点了?”
“老乡”?我突然感觉心口有一块冰冷的东西被融化开了,软软的。我迅速振作了一下,就像从蛇口逃脱的兔子慌忙甩掉皮毛沾上的肮脏的蛇唾液一样,看了看表:“下午两点了。”
“真慢啊!都四个小时了,还没到……”看来他已经急着回家了,他看看车窗外,“呵!这么大的雪啊……”
“雪已经停了。”
“你看外面地里那么厚的雪,下的时候一定大得很!”他凝视着窗外,望着那片阡陌不辨,被一座座孤零零的坟丘点缀得无比凄凉如同荒原的田地,我在他的眼睛里读出了担忧,就好像他有一件很宝贵的东西被冰封在雪盖下。
“是啊,瑞雪兆丰年!”我自作聪明地说着。
“就算年成再好,一到下大雪,我家的日子就不太好过。”他的视线垂了下去,似乎在研究被汽车轱辘溅起的泥泞,但那些奇怪的稍纵即逝的花纹太费神,于是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沉重的疲惫,在黑洞洞的瞳仁里坠得很深。“你家是市区的吧,”他接着说:“农村的穷人家是个什么样儿,你根本想不到。在下雪天,我家厨房的锅里都结着冰……”

我一听,哑口无言,原来我身边就坐着一位中原的农民。
他停了一会,好像想事情想累了,要休息一下,突然他又接着说:“年轻的时候一心想出去跑,可总被父母管教着,不敢走,现在在外面总觉得不是自个儿的地方,嫌不自在,又一心想回。家再不好也是家,得回去,我是出去打工讨生活的人,在外面过得再好,那也是讨啊!”
长途的颠簸让人疲惫不堪,在大巴把我送回家之前,我又迷迷糊糊的做了一个梦,仍很荒诞。
我还是在那片梦到过的荒原,我从战车上跌落,重重地摔倒在土地上,但我没有感觉到疼痛,我甚至感到一种软绵绵的温暖,起身一看,我竟站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,梦里不是冬天,微风含着成熟麦粒的馨香,抚起层层金黄色的麦浪,一直涌到天边,涌到同样黄灿灿的太阳底下,微风拂过麦芒,沙沙的就像阵阵遥远的欢呼,远处一座坟冢,在一片金黄的欢呼中坚定地站着,也许他站了几百年了,也许他还要再站几百年,他好像正在发表一段庄重的演讲,代替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先民和后生:“中原,我想你!”


- 散东西
- 暂无标签